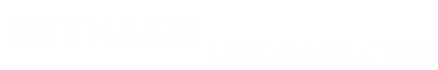
HASHKFK
BETHASH官方网站(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

倘若1976年就有了男性避孕药,那么我也许就不会写下这些东西。那一年,我的母亲(现已过世)在服用了12年口服避孕药之后,医生出于对健康的担忧,叮嘱她停药。父亲还记得,她对医生说,“可是我可能会怀孕的”。没过多久,母亲的肚子就有了“反应”。父亲的耐心解释让我觉得尴尬脸红。他说母亲停药后他们便转而使用避孕套,但“那玩意儿有时就会让你膈应得慌”,然后母亲便怀上了我。但如果那个年代就有男性避孕药的话,父亲说他一定会使用的。
20世纪70年代,连我父亲都有可能使用避孕药,某种程度上来说,男性避孕药的前景似乎非常不错。因为政府支持各种控制人口增长的理念,男性生育控制变成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其中有一种叫做棉酚(gossypol)的非激素药物可能是我父亲可能感兴趣的,而对棉酚的测试规模空前绝后。在1974年联合国世界人口大会上,艾利斯马·库提何(Elsimar Coutinho,如今是巴西的一位著名生育医生)推行棉酚这种药物。之前他在巴伊亚联邦大学(Federal University of Bahia)对男性志愿者进行了相关测试。然而,大家对于性与生育的态度是完全无法预测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男性避孕药的价值。
从20世纪60年代之后,库提何与中国政府一同开展了避孕工作。1972年,他们给8806名男性试用了棉酚药物,并取得了令研究人员满意的结果:日平均剂量成功降低了男性数量,但同时副作用也令人担忧。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其中66名男性血液呈低血钾状态【编者注:棉酚有良好的抗生精功能,但也存在两个主要副作用——低血钾,以及潜在的不可逆性(绝育)】。更重要的是,许多男性的数量在停药后并没有恢复正常水平。
爱丁堡大学的生殖学教授理查德·安德森(Richard Anderson)表示,一般来说有一些男性会使用男性避孕药,与之相对的一些女性也愿意相信他们,尽管媒体的报道通常有所不同。每当有新的研究报告发布时,新闻记者就走上街头随机采访妇女们是否愿意信任服用男性避孕药的男人,当然她们都一口否决。但如果你问的是她们是否会相信她们服用男用避孕药的伴侣,那个和她们一起抚育孩子,共享银行账户,每天同床共枕的男人时,那么你将会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
在1995至1996年之间,包括安德森在内的研究人员探访了爱丁堡、开普敦、上海与香港四个城市的1829名男性。开普敦的白人男性态度最为热情,8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至少愿意使用男性荷尔蒙避孕药。香港居民则最不愿意接受男性避孕药,只有40%受访者表示肯定或者或许会使用。而注射剂型的避孕药的吸引力则更少:开普敦60%的白人受访者与香港33%的受访者表示,如果这种药物需要注射的话,会导致他们更加不愿意采取这种避孕措施。安德森也认为这种避孕措施并不适用于每个人,这只是为大家提供一个可选择的途径而已。
安德森用一张照片揭示了注射问题的重要性。在照片中,一位妇女用注射器将激素注射到丈夫光溜溜的中,并且露出了得意的微笑。注射法是1991年安德森第一次参与世卫组织的临床实验中使用的方法。他表示这足以证明激素可以用于减少数量。同时,这项实验也证明了避孕并不需要将男性数量减少至零。数量为1500万/毫升算是正常值,实验中设定的最大阈值为300万/毫升。而现在的共识是,只要降到100万/毫升都可以算是有效的避孕措施。
安德森办公室墙上有一张褶皱的A4纸,纸上简要说明了激素类男性避孕药的工作机理, 即通过对大脑和睾丸进行调节来降低男性的生育力。对于大脑的调节中,主要是通过控制下丘脑与脑垂体,来减少相关激素的分泌。而在对睾丸的调控中,主要是抑制睾丸中产生睾酮的细胞,并且抑制细胞邻近的生精小管生成。女性避孕药中常用的孕激素用在男性避孕药中,可以抑制男性脑中的相关腺体停止分泌促黄体激素和促卵泡激素。若没有上述两种激素,男性的睾丸则无法产生以及分泌睾酮。所以该类避孕药在给药过程中会与睾酮类似物联合给药,以避免睾酮缺乏带来的肌肉无力以及消退等不良反应。
最终,欧加农与德国先灵(Schering)公司在2003至2004年间合作进行了大型临床试验。研究人员为297名男性植入了欧加农公司为女性研发的孕激素以及先灵公司的睾酮注射剂。并且给52名男性注射了安慰剂——所有参与者均采取了其他避孕措施,并监测数量。近90%接受激素避孕的男性数量已经降到了100万/毫升以下,而当试验结束四个月后,他们的生殖能力又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但这项试验并非一帆风顺。激素避孕组的男性比安慰剂组的男性出现了更多不良反应,例如痤疮,盗汗,对体重、情绪、性行为也有一些负面影响。一些参与者的症状极其严重,甚至有生命危险,其中包括一位企图自杀的参与者。
这段时间是两家大型制药公司研究兴趣的顶峰。2008年,在试验和发表结果期间,先灵公司被德国拜耳收购,之后便终止了这项工作。欧加农也同样结束了这部分工作,2000年之前,赫杰·寇林格·本尼克(Herjan Coelingh Bennink)一直担任该公司的生殖药物全球执行副总裁,他认为这项工作的终止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公司的支持。受安德森及其同事们调查结果的启发,寇林格·本尼克十分推崇这个方法,他还参与了实验的设计与评估。但它的经历与棉酚的命运差不多,欧加农高层的态度并不像其他地方那么开放。
离开欧加农后,寇林格·本尼克创立了万物皆流(Pantarhei,古希腊语,译者注)生物科技公司。在那里他时刻关注着女性避孕药的研发,同时为男性避孕药的开发提供灵感。女性开始使用避孕药时,可能会形成血栓。虽然风险很低,但一旦发生血栓,无论是对于女性还是制药公司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说,拜耳预计向使用避孕药产生血栓的女性诉讼者赔付约20亿美元。同样地,默克(Merck)和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也赔付了数百万美元来解决相似的事件。寇林格·本尼克表示,他们的新药“极有可能”可以帮助避免血栓。
据美国透明度市场研究(US-based Transparency Market Research)估计,2013年全球人民在避孕药具上共花费160亿美元。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是避孕装置,包括避孕套、皮下埋植避孕针以及宫内节育器(Intrauterine devices ,IUD)。同时艾美仕医疗信息研究所(IMS Institute for Healthcare Informatics)预计,2014年全球人民在抗癌药物上的花费约为1000亿美元,并且以每年6.5%的速度持续增长。而避孕药品消费额的增长率每年仅为1.3%,此外还有被起诉的风险,以及男性不应该服用避孕药的传统深入人心,所以寇林格·本尼克认为没有公司会愿意参与其中,“只能留给公共组织推行避孕药物研发了”。
另一个对这种药物感兴趣的赞助方是一家小型私人组织——帕萨默思(Parsemus)基金会(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其创始人伊莱恩·莱斯纳(Elaine Lissner)在阿莫比的研究与另一个前途光明的新型男性避孕技术两者之间犹豫不决。最终,她选择将基金会有限的基金用于资助后者。 阿莫比并不难过,因为他认为莱斯纳是人们仍然在谈论男性避孕的主要推动力。但莱斯纳仍然感到十分遗憾,“这么多年以来他们这个预防艾滋病传播的新颖想法还得不到支持,这简直令人震惊。”
这种被称为Vasalgel的输精管凝胶会使得顺利通过却会截留,当男性需要恢复水平时,可以通过另一次注射来洗脱凝胶。倘若一段时间没有高潮,通常受阻的会在附睾中被清除,并且被免疫细胞吞噬。莱斯纳积极推广输精管凝胶,只要浏览一下输精管凝胶的Facebook,就绝对不会怀疑男人们对它的兴趣 。她说:“人们热切期待Vasalgel输精管凝胶。我们的邮件列表上就有超过32000人等待临床试验。”
30岁的已婚机械师贾斯汀·特瑞(Justin Terry)在阿拉巴马州制造车辆零件,他十分渴望尝试该药物。他与妻子没有孩子,妻子正在服用避孕药。贾斯汀表示他们已经结婚十年,双方都不想要孩子,然而她不想再吃药了。避孕药使得他妻子的十分脆弱,她担心继续服用会有不良反应。由于辅以激素药物,贾斯汀注射了Vasalgel输精管凝胶之后,仍会游动数周,但这并不会使他困扰。他曾经考虑过输精管切除术,但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犹豫,因为这不完全可逆。而Vasalgel输精管凝胶是可逆的,并且只需要微创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