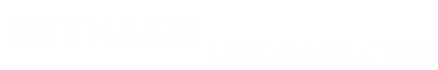
HASHKFK
BETHASH官方网站(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

在年轻人出国留学热度每况愈下的今天,中老年人正在“逆势出海”,他们对继续教育的热情高涨,这从中老年教育培训市场供不应求的状态中可以看见:2024年武汉中老年人凌晨4点排队报名老年大学;贵州11万中老年人抢千个大学名额;杭州的中老年人甚至要摇号抢热门课程名额;上海2.5万个老年大学名额,一秒抢空。一些外语培训机构开设“熟龄留学项目”,发布中老年留学攻略,介绍说“留学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属”,50岁以上也能通过留学“实现自我成长和职业提升”,
比游学更硬核的是正式留学获得大学学位,像王晓西这样考上正规大学的中老年人不在少数,他们也在社交媒体上留下了海外留学的生活轨迹:五十岁网友“圆蛋春卷”和丈夫双双申请了荷兰莱顿大学考古学专业,2024年已经成功升入大二;六十多岁的网友“来美国留学的老阿姨”记录了自己读美国私立大学文科、社区大学计算机专业的过程,她的目标是转入州立大学取得本科学位来完成她年少时未完成的梦想,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海外留学“没有老年大学的人情世故、争风吃醋。缺点是你常是最慢最笨的那个”。
女儿小雨不放心我一个人生活,公司允许她远程办公,于是她决定在我申请学校的阶段就搬到雅典和我同住一年,做“陪读女儿”。她给我买了智能手表戴着,说如果我出危险,比如晕倒,她能马上知道,这两天她又要给我再买一个智能戒指,说能连续观测我每天晚上睡觉的体温和心率变化,她还把我所有要吃的营养片剂、药物都用标签分门别类贴好、摆整齐,方便取用。为了确保出差时也有人能看顾我,她又找了可靠的邻居,一个雅典公务员,每天上班下班时上门向我问好,确定我的身体情况。
我的亲妹妹也很支持我留学,又出钱又出力说要给我出一半的学费。我原来不准备收的,但小雨建议我把这笔钱当成“家庭半额奖学金”来看待,她笑说这样我就有学习压力,因为“要给大姨一个交代”,所以“每门课都要考A”。妹妹曾经是高三英语老师,也是物理学硕士,十年前罹患急性脑脊髓炎后不能行走,可是她对自我的要求没有放松,每天坚持超过3个小时听BBC新闻、啃英语原著。五年前她就鼓励我每日打卡学英语,不时给我发大红包奖励,她和女儿一起变成了我的英语顾问。
申请雅典大学要提交很多材料,我翻出了四十多年前的高中成绩单,先用中文写了一遍申请文书,再请ChatGPT用英文翻译出来,小雨来校对。大学招生办公室很快就给了回复,3位教授要在网上对我进行全英文视频面试。面试当天早晨,小雨突然问我,如果招生官问你,这么大年纪还想重回校园,知道自己的困难在哪里吗,你该怎么回答。我认真想了想答案: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被社会责任和他人的期望所驱使,但现在我想追求一些真正让自己兴奋、能满足自己的事情,而我相信这永远都不会太晚。
结果执行第一天我就觉得要昏倒了——凌晨3点半起床,看国内A股的情况,4点半看英语新闻、课件,背单词;5点半到7点稍微休息;7点到8点给猫咪喂饭、准备早饭、收拾房间;8点出门,40分钟步行去学校;第一堂课就是希腊口音最重的历史教授上课,我要连续听3小时的“天书”到12点结束,教授PPT特别多,一上课我就成了拍照机器,不停啪嗒啪嗒,拍好了回家再细品;12点20分之前赶室上考古课,一直上到下午3点钟,下一堂现代希腊语课是6点开始。当时我已经开始脑袋疼、耳鸣了,但我还想看看这3小时能在校园里做些什么,接着就去图书馆看书了,等到彻底下课从教室出来天已经黑透了,回到家是晚上9点钟,我澡都洗不动了倒在床上就直接昏睡过去,一口气睡了12个小时……后来我再没执行过这个计划表,还是放过自己吧,身体最重要。
一学期的时间很短,况且我还有专业课要消化,形势相当严峻。于是每天放学,小雨都会问我今天课听得怎么样,每次我做完作业,她都要帮我检查,有时候我觉得作业好难,想让她帮我写算了,但她坚决不同意;她同时也在着手帮我制定雅思考试计划,催我背单词,每天都在家给我模拟雅思口语考试。就算出差也不肯放过我——她刚离开希腊没两天,她留过学的好朋友A就在微信上跟我说,王阿姨,小雨给我布置的任务,我们今天要来练雅思口语。那一刻我厌学情绪爆发,甚至找借口说“要不让我先做会儿家务吧”……可小A不理会这个借口,坚持完成了我的模拟考试。
过去我是个老师,学校开家长会要留下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家长面谈,我那时候总是对小雨说,你不能考得太差,起码不能让老师找家长,这样我太没面子了。现在这些话都返回到我身上了,羞耻感也变成了我的“学习动力”。开学没多久,有一次历史课老师随堂测验,我只考了40分——开学前两周,我一直处于“听天书”的状态,我的录音笔可以立刻把语音转写成文字,但老师的希腊英语口音太重,录音笔都听不懂,那次我甚至没有听明白老师说要随堂测验,毫无任何准备就上阵了。小雨狠狠批评了我,她说,第一,你的时间花在哪里是可以看见的。第二,这个专业要是读不下去,小红书上就没法更新,学霸人设要崩,很没面子的。
小雨以“过来人”的身份教育我要知足,她说,“你看你现在留学条件多好”,“你都不知道我当年是怎么过来的”,“实名羡慕你们这一届留学生已经有ChatGPT这样的AI来帮你想文章结构”。但其实我这个年纪用电子产品、电脑系统困难重重,小雨都说我是“电脑苦手”。现在的大学课程一切都数字化了,我这个戴老花眼镜的苦手一开始看到要用一大串密码登陆学校的希腊语系统做作业、找文献,整个人是懵的,就像看加密文件一样。所以我还是找小雨帮忙。课程PPT、作业、资料书单有大半都是她帮我下载的,看电子版我感觉头昏眼花,她就把8本主要的教材找便宜的淘宝商家打印出来,再让我先生假期时人肉背来希腊。
不过我还是给自己准备了不少先进电子设备,比如录音笔、iPad(以前就有的)、Kindle(最后没用上)、一台“新”电脑(儿子淘汰的)。小雨吐槽我,“差生文具多”。开学第一周,一上课我就想着启动这些设备,但按什么按钮启动、调节音量……一通手忙脚乱,而且我只会用两根食指打字,打字速度完全跟不上教授的语速,我看了看周围同学,他们都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快速打字,只有我用笔再我的笔记本(纸质的)书写。坦白说,我无法同时使用两件以上的电子设备。直到有一天我忘带手机去上课,发现丝毫不影响学习,但老花镜没有带,真就是两眼一抹黑,什么都看不清,我才意识到原来只有老花眼镜才是上课的刚需。
老龄留学有时也会让我回到做老师的感觉。班上同学大部分是06年左右出生的,而我在学校教的最后一批学生也已经是83、84年的,也就相当于我学生的孩子现在做了我的同学,这些孩子叫我“王阿姨”已经是很客气,最近有个中国同学问其他人“你有那个60岁老奶奶的微信吗?我加一下,我得问一下那个拉丁语作业咋写”,我的辈份又往上提了提。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也习惯性会去指出来,像有个同学上课大声跟同桌说话,课下还总是和几个男生关起门来打游戏,这让我想到了以前我儿子也是网瘾少年。我在想是不是要和他们谈谈,让他们出来一起参加集体活动。
现在总是会听到“35岁门槛”“40岁危机”这样有关年龄的歧视性表达,这实际上是等级社会中必然会存在的游戏规则。我从来不在乎、也不愿意被迫遵守这种游戏规则,过去做教师评职称就有年龄这条限制,我宁可不评,因为觉得没有意义。虽然年龄并不能在意识层面上去限制我想做的事情,但我也不得不面临身体衰老的现实。曾经我有两样特别自豪的东西,一是视力,二是记忆力。50岁左右,我的双眼视力从1.5变成了一只近视一只远视再加上双眼老花,而且我开始丢三落四,甚至和人说话时说着说着会找不到线岁,每次下课回家,我要马上回忆一下老师上课说的重点,不然就会忘得一干二净,接着我还要安排做英语阅读,可是一看文章我就容易睡着……这些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因为眼睛和脑子是很重要的学习工具,现在因为功能衰退,我要花比年轻时多好几倍的力气学习。开学前,我和家人在雅典疯狂city walk,开学之后,我先生每到周末都想和我一起出去玩,我严词拒绝,因为这样学习要跟不上了;我一些住在欧洲的朋友希望开学以后来看我,说要观察我这个大龄学生怎么在希腊雅典上大学,我热情接待,过后发现太影响学习,现在准备拒绝所有社交。
我学生时不好会难过到默默流眼泪,再默默努力迎头赶上。不过现在我不会流泪,也不会再勉强自己了。我和家人达成了“不硬撑共识”,承诺不再非要把某件事情做好、做完,那样自己倒下了会弄得家人都“鸡犬不宁”。所以某天的课没复习、作业没交,老师如果愿意放我一马,我会很感谢,如果对我严格要求,给我不及格,我也不会抱怨或者崩溃。我很清楚客观条件就是这样,我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了。马拉松运动员没有规定要花多长时间完成比赛,我念的项目最多可以读6年,如果6年可以完成“留学马拉松”,我觉得也很好。
我有个与众不同的父亲。他在我未成年的时候就反复强调,不要因为自己是个女孩子就觉得这不能做、那不能做,你都可以做,不过做事之前要先问问他的意见,因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有知情权,也是审查者。父亲非常通情达理,对很多事情都有很大的包容性。他在兵团农场工作,是个喜欢读书的机械修理工,他说,等你长大了可以完全自己做决定,只是需要去承担相应的责任。也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之下,我和妹妹们都有很强的个人意志,小时候很调皮,爬墙骑马、上房揭瓦,我经常会跟小雨调侃过去的事,“我爸三天没有打我了”。
不久之前,我在古希腊语课堂上学到了一个词叫“婚姻“,从词的构成来看,词根是一个表示“男人”的词语,古希腊人在词根前加了“under”,说明了古希腊人理解的婚姻,就是“在男人之下”。教授说虽然从现在看这是不公平的,但对于那时的女性而言婚姻正是如此。当下,很多男性依然会害怕驾驭不了像我这样有很强自由意志的女性,而且不认为女性是可以平视的伙伴,和男性拥有平等的权利。我也知道《出走的决心》,里边的苏敏50岁离开家庭去全中国自驾游,如果你去问一个像苏敏丈夫这样的人,是否可以做某事(比如在56岁去希腊留学),他永远都不会支持,甚至还会鄙薄你——当苏敏走入婚姻之前,她已经被原生家庭和社会环境塑造成婚姻中的奉献者和牺牲者的样子了,也是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当她要成为一个受尊重的完整的人时,做的第一件事情当然是在婚姻中对抗丈夫(其实是社会强加给女性的道德伦理教条),以及去颠覆原生家庭帮她塑造的女性意识,自我意识觉醒,找到真正的自己。在上海,另一个叫做沙白的女性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更加极端,不仅拷问了自由选择生活地点、方式、配偶的权利,还拷问了自主选择死亡方式的可能性与宽容度。她俩的事例就像给“过去”的两记耳光。
当然,我先生也不可避免地出生在一个男尊女卑的传统家庭里,但我与他交往时发现他有脱离原生家庭的对女性的尊重,这一点让我们可以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平视对方,不限制对方的个人发展,互相补位。比如先生早年考到上海念MBA(工商管理硕士),我愿意在家带孩子;我选择去考研究生,先生在家照顾孩子,周末带小雨出去玩,在家里做饭、打扫卫生;后来我决定去新加坡工作,带着刚上小学的女儿,他就继续攻读博士。我这次决定在希腊留学,他在上海处理自己的工作,合理安排我们的假期团聚。在这个家里,我做的事情都是自己选择的,包括儿子学习动力不足,我辞职在家做他的“陪读妈妈”,直到把他送进大学;未来小雨结婚、生孩子,我愿意从她怀孕开始陪伴她,一直到帮忙带她的孩子……我不认为这些是为了孩子牺牲自我,这是我生命旅程中的功课,惊喜和烦恼共享,这些更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成就。
即便我先生已经是个很好的人,但一些传统的印记受家庭影响下意识地反映在细节中。比如我先生总是不太愿意夸赞我,认为整体上我是不能超过他的,只是偶尔说“你还可以”,我就会回怼,我在很多事上一直聪明,只是你不愿意承认。冲突也不可避免,但大多是因为我们上一代人介入我孩子的教育问题。比如婆婆希望我儿子、她唯一的孙子在春节时做一些孝道,我先生不敢吱声,我就会和他有激烈争吵,这样的事情发生多次,我就画了一条清楚的界限——我要求她距离孩子们的生活远一点,逢年过节才去探望。除了这一点共识之外,在很多其他问题上我并不完全要求先生改变自己。我会告诉我的孩子,人和人都是不一样的,你可以选择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所以如果看见爸爸妈妈有冲突,可以把我们理解为一面引发你们思考人生的镜子。
眼下我有了一个“小目标”,之前还没被大学录取的时候,朋友们到希腊旅行,我陪他们去看考古博物馆,带着他们按照自己设计的路线参观,按照时间顺序从最老的一栋建筑开始,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停下介绍。这好像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开始留意那些导览工作人员怎么介绍博物馆里的内容,这些都是我后来专业课的内容。在听的过程中我在想,假如我今后也能做这样的工作,我该怎么讲,这感觉就像中国人练书法先要模仿字帖一样——向人介绍一个国家的文化,是我觉得很有意义、很有趣的工作,这里雇佣员工也不分年龄,假如我60岁毕业,说不定也能被博物馆雇佣呢?我之前还和朋友夸下海口,说要考出欧盟导游证。据说这张证特别难考,至少要精通2门外语,还要对欧洲的人文历史非常熟悉,考出来以后或许能在博物馆工作,成为一名文化使者,这就是我现在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