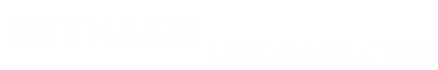
HASHKFK
BETHASH官方网站(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

关于独创性这一概念,存在着独创性有无与独创性高低两种思路,当前理论及实务界更多接受独创性有无观点。一般来说,独创性所要求的“必要的创造性的量是非常低的,即使微小的量也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作品都能够很容易达到这个程度,因为它们闪烁着某种创造性的火花。”例如,上海浦东法院在体育赛事画面版权纠纷案中指出,《著作权法》对于作品独创性的要求应该是最低限度的,而非一个抽象的、无法捉摸的“较高独创性标准”,只要是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就满足了最低限度独创性的要求,这也符合该法激励创作的基本立法宗旨。
基于著作权理论及司法裁判所确立的原则,可作出如下归纳:独创性不等于作品艺术性的高低,法律并不对作品的审美价值或经济价值作出评判。一般而言,独创性系指在具备个性化创作空间的前提下,作者依据自身意图对表达元素进行独立的选择与编排,即可认定具备独创性。所谓个性化创作空间,系指存在对表达元素作出独立选择与编排的可能性;个性化创作则指作者依其独立构思对表达元素进行选择与安排。而“一定的智力创造高度”所强调的是,创作须源于人的智力活动,而非机械性记录,并须具备最低限度的独特性。
周围表示,2024年,网络微短剧行业迎来了井喷式的发展,其市场扩张速度与用户渗透能力超出了行业预期,成为数字内容消费领域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根据DataEye《2024年微短剧行业白皮书》,2024年中国网络微短剧市场规模预计达到50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9%,并首次超越同期内地电影票房总额。行业预测显示,这一市场规模有望在2027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与市场规模同步扩张的是其庞大的用户群体。
但是,由此产生的侵权行为也是乱象丛生,侵权模式呈现类型化。如直接盗播与“搬运”,这是最原始也最直接的侵权形式。“切条搬运”相较于完整搬运,这种模式更为隐蔽。“翻拍式抄袭”,此类行为涉嫌同时侵犯原作的复制权和改编权,是司法实践中认定的难点。改编侵权,微短剧产业链中,大量剧本改编自网络小说。未经原著作者许可,擅自将其文字作品改编并摄制成微短剧的行为,直接侵犯了原著作者的改编权和摄制权。AI赋能的新型侵权,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催生了新的侵权样态。
网络微短剧的版权治理并非一蹴而就。它要求所有利益相关方——创作者、平台、监管机构、司法部门和行业组织——摒弃孤立作战的思维,通过制度建设、技术创新和协同合作,共同编织一张细密而坚韧的保护网络。这一过程,不仅是对现有法律秩序的维护,更是对行业未来发展模式的重塑。通过系统性地提升侵权的成本与风险,同时降低原创与合规的门槛与成本,才能真正引导微短剧行业告别“野蛮生长”,迈向一个以原创IP为核心价值、具备长期生命力的精品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在权属认定方面,存在完整证据链与署名孤证之二分。在原告提交完整证据链场景下,根据原告提交的联合开发协议、拍摄协议、联合出品协议及版权声明等相关材料,依法认定权利归属,无需先行将微短剧归入“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或其他视听作品”之具体作品类型。在署名孤证场景下,则需对相关作品类型进行核查,属于其他视听作品的,应按照其他视听作品的权利归属规则,重点核实是否存在特定约定等事实。此时不宜适用署名推定+反证的传统认定规则,否则将导致举证责任转嫁至被告一方。
实质性相似比对:在微短剧侵权纠纷中,因翻拍或改编涉嫌侵权的,法院需从“质”与“量”两个维度进行实质性相似比对。主要涉及思想与表达的界分,判断被告未经许可使用的部分究竟是原告作品中的思想还是表达。在“质”的层面,人物设置和情节只有具体到一定程度,才能构成著作权法上的表达。套路式、框架式抄袭或相似的情节之处仅能概括到相对抽象的层级,可能因落入思想或公有领域而被排除,难以认定实质性相似。在“量”的层面,需要考虑紧密贯穿的情节设置在被诉侵权作品中是否达到一定的数量、比例或者受众是否足以感知到来源于权利作品。
关于微短剧行业现状,马妍介绍,截至2024年12月,微短剧用户规模达6.62亿,2024年市场规模首次超越中国电影全年总票房,2025年预计市场规模将突破680亿元,市场规模与用户粘性持续增长。政策层面,国家广电总局推动“微短剧+”计划,赋能千行百业并创造60万就业岗位;内容层面,正向精品化转型,如《家里家外》以地域特色与人文情怀创10亿播放量;商业模式层面,从付费主导逐步过渡到“免费与付费并存”,红果短剧通过“免费+广告”模式单月分账破亿,成为行业标杆;传播渠道层面,30余部微短剧登陆省级卫视,并形成联动生态;市场格局层面,短视频、长视频、电商等多平台布局形成多元竞争生态,推动规模持续扩张。
在司法争议层面,以“万国觉醒”与“三国志”案件为例,两案一审均认定游戏玩法构成著作权保护对象,二审却完全推翻,核心分歧在于游戏玩法的法律属性认定。法院通过“接触+实质性相似”标准判定侵权,但二审强调游戏玩法多属“思想”或“操作方法”,依据著作权法“思想表达二分法”不予保护。该原则旨在平衡创作传播、排除专利保护范畴、鼓励二次创作与市场竞争,但反不正当竞争法(简称“反法”)的适用可能加剧保护边界模糊——反法以“诚实信用”为原则,保护客体不明确,权力边界、合理使用及保护期均无明确标准,易导致司法裁量差异,影响法律稳定性。
在保护路径层面,需区分游戏元素的法律属性:思想范畴如题材、主题、类型(如战略游戏)不受保护;功能性要素如游戏规则(如11人制足球规则)属于专利领域,不纳入著作权;必要场景元素如跆拳道游戏的标准化动作,因独创性不足亦不保护。反之,高独创性表达如角色设计(如“吃豆子”怪物特征)、画面构图(如俄罗斯方块的颜色组合与长宽比例)、情节编排(如道具升级路径的具体设计)可受保护。国内案例亦印证此逻辑,如“金庸奇侠传”游戏因擅自使用金庸小说角色被认定侵权。